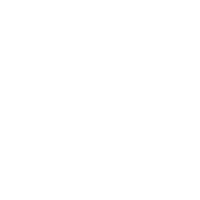I. 引言:替代方法与3R原则的科学与伦理背景
1.1 实验动物使用的伦理基础与3R原则的演变
实验动物的使用在生物医学研究和药物开发中具有悠久历史,但同时也引发了重大的伦理关注。规范这一领域的指导方针是1959年由Russell和Burch提出的3R原则(Replacement, Reduction, Refinement,即替代、减少、优化) [1, 2] 。这一原则构成了动物实验伦理的核心基础,要求只有在没有其他合适的替代方法可用时,才允许进行动物实验,并且动物的数量和所承受的痛苦必须限制在最低限度 2 。
替代(Replacement)策略是3R原则中追求的终极目标。根据其实现程度,替代可细分为“相对替代”和“绝对替代” 3 。绝对替代指的是在实验的任何阶段不使用有感知能力的活体脊椎动物 3 。然而,DFG(德国研究联合会)等权威机构强调,持续应用3R原则与科学自身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实验动物福利受损反而会损害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重复性 2 。这意味着,实施3R原则,尤其是寻求替代方法,必须以不牺牲科学严谨性为前提。如果新型替代方法(NAMs)在模拟人体生理功能上存在重大缺陷,那么追求“绝对替代”将与其保障科学质量的核心伦理诉求相冲突。因此,替代方法的有效性是其取代动物模型的先决条件。
1.2 动物模型在药物翻译中的固有局限性
对动物模型进行绝对替代的呼声,不仅源于伦理考量,更关键的是基于动物模型在预测人体生理和病理反应方面的固有科学局限性 4 。长期的药物开发数据显示,超过90%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安全有效的药物,最终在人体临床试验中因安全或疗效不足而未能获得美国FDA的批准 4 。这种高失败率凸显了物种间生理差异带来的翻译困境。
特别是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癌症和炎症性疾病等常见病领域,动物模型数据的预测性尤其不准确 4 。例如,某些在人类中被广泛认为是安全的药物,如阿司匹林,如果按照严格的动物测试标准,可能无法通过测试;相反,一些在动物模型中表现安全的化合物,在人体试验中却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如TGN1412事件) 4 。此外,实验动物,特别是常用的啮齿类动物模型,通常具有高度的近交性(inbred nature),与人类巨大的遗传多样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导致药物代谢和靶点作用结果差异,进而造成翻译失败的重要因素 6 。因此,NAMs的兴起,旨在提供更具“人体相关性”的模型来弥补动物模型的这些科学缺陷 4 。
1.3 新型替代方法(NAMs)的兴起与监管趋势
新型替代方法(NAMs)包括体外人体系统(如细胞培养、类器官、组织培养)、微生理系统(MPS或芯片器官,Organ-on-a-Chip)和计算模型(如计算机模拟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in silico modeling) [4, 7] 。这些方法利用人类细胞或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Cs),旨在更可靠地反映人类生理学、疾病特征和药物基因组学 6 。
全球监管机构已认识到利用NAMs提高预测准确性和加快药物开发的重要性。例如,美国FDA通过《FDA现代化法案2.0》以及后续发布的路线图,战略性地鼓励采用NAMs [8, 9] 。FDA的目标是利用NAMs的优势,克服动物模型预测失败的缺陷,从而在进入昂贵的动物实验阶段之前,进行早期、更准确的风险评估 4 。NAMs,如通过人工智能预测免疫原性或通过肝脏芯片检测肝毒性,可以帮助筛选掉高风险分子,从而达到精简和加速药物开发的目的。然而,这种战略方向旨在实现对动物使用的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而非完全取消动物验证,这一关键区别构成了NAMs无法实现绝对替代的根本原因。
II. 新型替代方法(NAMs)的技术局限性分析
NAMs,特别是类器官(Organoids)和微生理系统(MPS),尽管在模拟特定组织结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模拟完整的体内环境时,仍面临难以克服的结构和功能障碍。这些障碍严重限制了它们在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中取代整体动物模型的能力。
2.1 缺乏系统整合:循环、免疫与神经轴的缺失
要准确评估药物在人体内的行为,必须考虑药物在全身的动态过程及其对多个器官系统的影响。然而,当前的类器官和单器官芯片模型普遍存在关键系统的缺失 10 。它们通常缺乏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这使得研究者难以研究不同生理系统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即“串扰”,crosstalk) 11 。例如,单器官芯片无法再现脑-肠轴等重要生理轴的交互机制 11 。
这种系统级缺失在药物毒性评估中是致命的。药物的许多严重不良反应,例如全身性炎症反应或免疫介导的毒性(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本质上是全身性事件。由于NAMs缺乏集成且成熟的免疫细胞群,它们无法准确预测此类风险 5 。只有在整体生物系统中,药物才能经过完整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过程,并触发全身性的反馈和代偿机制。因此,缺乏这些系统整合能力的体外模型,无法捕捉到药物的全身性、非靶点效应,在最终的系统毒性验证中仍需依赖动物模型。
2.2 血管化缺失与坏死核心的形成机制
类器官的结构限制是其无法取代动物模型的核心障碍之一。由于缺乏内在的血管化(Vascularization),类器官内部的细胞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和氧气供应,导致形成坏死核心(necrotic cores) 10 。在体内,血管系统不仅负责输送营养和氧气,还是清除代谢废物、维持组织长期活力的关键。
坏死核心的形成限制了类器官模型进行长期、慢性病理或毒性研究的能力。许多重要的毒理学研究,例如致癌性或生殖毒性评估,要求对生物体进行数周乃至数月的药物暴露观察。体外模型在缺乏长期、稳定血液灌注和废物清除机制的情况下,无法保持细胞的长期生理功能,使得它们无法替代那些要求长期、全身暴露的动物实验 1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多器官芯片(MOOCs),即“人体芯片”的概念,以期整合血管网络、免疫细胞和多器官系统,但这些复杂系统的设计、维护和长期稳定性仍是当前巨大的技术挑战 10 。
2.3 标准化、可重复性与高通量挑战
在要求极高标准化和低变异性的监管环境下,NAMs当前的技术成熟度面临严峻的挑战。生物学复杂性虽然使3D模型更具价值,但也使得大规模实验的可重复性管理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12 。
具体而言,类器官的培养通常依赖于基质胶(如Matrigel),这种材料的环境控制有限,容易造成批次间的差异,从而显著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 10 。另一方面,芯片器官技术需要专业的微加工(soft lithography)和微流控操作,这些技术对资源和专业知识的高度依赖,限制了其在普通实验室中的大规模复制和高通量应用 10 。此外,尽管体外模型可提供标准化的分析环境,但其细胞组成往往相对均一 [11, 13] ,难以捕获体内组织所具有的复杂外细胞基质和基质细胞组成,以及天然的克隆和遗传异质性 13 。因此,NAMs在批次间变异性和高通量操作上的不稳定性,使其难以成为普遍接受的、可大规模复制的最终监管验证工具。
以下表格总结了现有体外模型在模拟复杂生理系统时面临的关键技术局限:
Table 1: 现有体外模型(NAMs)在复杂生理系统模拟方面的技术局限性对比
|
局限性维度 |
类器官模型 |
单器官芯片 |
多器官芯片 |
支撑数据 |
|
缺乏关键系统 |
免疫、神经、循环系统缺失 10 |
缺乏全身循环和系统性串扰 11 |
整合复杂性高,维护困难,仍难以完全复现全身生理轴 10 |
10 |
|
营养与氧气供应 |
易形成坏死核心 10 |
依赖微流控,需精确设计和维护 10 |
流量控制与细胞活力维护难度高,难以支持长期研究 |
10 |
|
重现性与标准化 |
依赖基质胶,批次间差异大,基因漂移风险 [10, 12] |
需专业微加工技术,资源受限 10 |
细胞培养与微环境控制高度复杂,影响结果可靠性 14 |
[10, 12, 14] |
III. 药物代谢、药代动力学(PK)与毒理学评估的系统性挑战
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是一个动态的全身性过程,涉及复杂的药代动力学(PK)过程:吸收(Absorption)、分布(Distribution)、代谢(Metabolism)和排泄(Excretion,简称ADME)。由于NAMs无法全面模拟这些动态过程,它们无法承担药物的最终PK和系统毒性评估任务。
3.1 药物吸收与分布(AD)的体外预测限制
药物的临床前评估必须涵盖溶解度、蛋白结合、血清稳定性等特性,以及ADME过程,这对于结构-药理/性质关系(SPR)的评估和化合物的优先级排序至关重要 15 。
在药物吸收方面,Caco-2细胞渗透性检测是行业内预测肠道药物吸收的标准体外模型。然而,该模型本身具有显著的局限性:Caco-2细胞需要超过20天的广泛培养,并且常常无法形成均匀、内聚的单层结构以保证化合物的统一转运 15 。更重要的是,该检测需要消耗大量的化合物(通常约20毫克) 15 。这些操作上的复杂性和对化合物数量的高要求,降低了Caco-2模型在早期药物发现阶段的实用价值。此外,体外模型只能提供药物内在吸收潜力的片面指标,而无法反映药物在全身循环中与血浆蛋白、多种组织隔室的动态分布和组织渗透性。药物的真正功效和毒性依赖于目标部位的实际暴露量,而这只能通过整体动物模型提供的PK曲线和生物利用度数据来全面确定。
3.2 代谢、清除与多器官串扰的复杂性
药物的代谢和清除是系统性毒性评估的关键环节,涉及肝脏、肾脏等多个器官的协同作用 11 。药物毒性往往并非由原药引起,而是由其代谢产物引发,或者是在清除通路受损后导致的间接多器官损伤。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了利用iPSC衍生的3D肝脏模型(如肝脏芯片或类器官)来研究药物代谢、药物-药物相互作用(DDI)和清除过程 16 。然而,目前最大的挑战仍然是生成在生理和病理上与功能性人体肝脏高度相似的模型,并确保其细胞活力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16 。为了应对更复杂的药物过程,多器官芯片(MOOC)——“人体芯片”的概念应运而生,试图模拟涉及多个器官的更全面生理条件 11 。然而,由于MOOCs在集成血管化、免疫细胞群和长期维护方面的复杂性尚未得到可靠解决,它们目前难以模拟药物在体内完整的半衰期、活性代谢产物生成和下游器官(如代谢产物对肾脏的毒性)的系统性清除影响。
3.3 整体动物模型在毒理学终极验证中的必要性
NAMs在早期筛选中展示了识别人类特异性毒性的潜力,有助于避免使用动物模型可能导致的误导性结果 4 。然而,在药物进入临床试验之前,监管机构需要对药物进行终极的哺乳动物安全性测试,以捕捉涉及复杂系统相互作用的或长期暴露下的毒性。
现有体外模型,包括干细胞衍生的模型,由于细胞成熟度不足(尤其是肝细胞样细胞),目前尚不能广泛应用于解决复杂且不可预测的脱靶毒性问题 5 。研究发现,通过对比药物对人类类器官和动物类器官的作用,可以指导研究者选择最具相关性的动物物种进行后续体内验证 17 。这种方法清楚地将NAMs定位为辅助和去风险化工具,而非绝对替代品。只有整体动物模型才能提供药物在多器官、多系统相互作用以及长周期暴露下的毒理学和药代动力学全貌,满足监管机构对最高级别安全保障的法律和科学要求。
IV. 特定复杂疾病领域中动物模型的不可替代性
在涉及认知、行为、全身免疫和复杂疾病进展等高度依赖系统整合的领域,NAMs与动物模型的差距尤为显著。
4.1 神经科学与行为研究
神经科学研究的核心在于理解意识、学习、记忆和复杂的行为反应,这些都属于整体生物系统独有的“涌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非人灵长类动物在理解大脑发育、功能和复杂行为方面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 19 。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艾滋病、癌症等涉及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疾病的治疗研究,仍需要高等动物模型 19 。
尽管类器官可以在细胞层面模拟神经元连接和初级组织结构,但它们无法重现或评估药物对全身行为(如焦虑、抑郁、睡眠模式或药物依赖性)的影响 20 。在涉及中枢神经系统(CNS)的药物研发中,药物的穿透血脑屏障的能力、药物在神经回路中的长期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变化,只能在完整的、有感知能力的生物体中观察和测量。因此,在评估CNS药物的安全性和功效时,高等哺乳动物模型是不可或缺的。
4.2 复杂免疫疾病、疫苗开发与全身炎症反应
免疫系统是一个高度分布和动态的系统,其功能涉及全身淋巴器官的协同作用、循环系统中的细胞运输和复杂的信号级联反应 11 。由于NAMs通常缺乏完整的免疫细胞群和循环系统 10 ,它们难以模拟全身适应性免疫反应或全身炎症反应。
疫苗的开发和免疫调节药物的评估需要一个能够产生适应性免疫反应的完整宿主。著名的案例显示,即使是动物模型,在预测人类免疫反应方面也存在挑战,例如针对AIDS的疫苗,黑猩猩和猕猴模型的预测失败率高达100% 21 。物种间的生理差异(如TGN1412事件所显示的细胞因子风暴差异)更是凸显了系统性免疫激活预测的难度 4 。然而,尽管动物模型的预测性并不完美,在目前缺乏能够模拟完整淋巴器官、T细胞激活和全身信号传导的体外系统的情况下,动物模型仍然是评估疫苗原性和免疫安全性的唯一已验证平台。
V. 监管框架与“绝对替代”的差距
全球监管机构的最新政策和路线图清楚地表明,它们对NAMs的应用定位是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现有的动物测试,而非绝对消除(Absolute Replacement)。
5.1 FDA现代化法案2.0下的NAMs应用定位
美国FDA的《FDA现代化法案2.0》以及其发布的路线图,旨在通过鼓励使用NAMs,如芯片器官系统和计算建模,来减少临床前安全研究中的动物测试 4 。这一举措的科学依据是动物模型在许多常见疾病和药物(特别是单克隆抗体,mAbs)的预测中存在严重缺陷 4 。
FDA的战略是将NAMs作为提高药物开发效率和人类相关性的工具,以实现“加速治愈”和“减少动物使用”的双重目标 8 。通过在早期利用NAMs,研究者可以更有效地评估免疫原性或毒性潜力,从而筛选掉高风险分子,减少进入昂贵且耗时的动物实验的化合物数量 4 。然而,美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NABR)明确指出,《FDA现代化法案2.0》允许使用非动物测试方法是基于“可行性”的原则,但“并未消除对动物测试的需要”,并强调“动物模型仍然是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必需品” 8 。这表明,监管实践仍处于追求Reduction的阶段,尚未为Absolute Replacement做好准备。
5.2 动物模型在当前IND/BLA申请中的法律与科学要求
监管框架的核心使命是确保公众健康和药物安全。在药物进入人体临床试验(IND)或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之前,必须提供全面且可靠的安全性数据。当前,NAMs缺乏提供完整的PK/ADME和系统毒理学全貌的能力。
因此,NABR的观点具有指导意义:目前在生物医学研究和药物开发中,“没有可以完全取代动物模型的替代品” 8 。国际监管指南,如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和FDA,在评估先进治疗药物(ATMPs)的功效、持久性、剂量反应和安全性时,仍然推荐在后期开发阶段使用大动物模型(如猪、绵羊或马),因为它们提供了更贴近人类生理的尺寸和结构相似性 18 。只有整体动物模型能够提供药物在多器官、多系统相互作用下以及长周期暴露下的全面安全性和功效数据,这使得动物模型的最终验证成为当前实现监管合规、保障人类受试者安全的科学和法律必需品。
Table 2: 监管机构对实验动物使用政策的最新立场和科学依据
|
机构/法规 |
核心政策定位 |
对NAMs的态度 |
对动物模型的必要性声明 |
支撑数据 |
|
3R 原则 |
伦理与科学质量的整合 2 |
推动绝对替代作为长期目标,但强调科学有效性 [1, 3] |
在缺乏其他合适方法时,动物实验是必需的 2 |
[1, 2, 3] |
|
美国FDA |
减少动物使用,提高人类相关性 4 |
鼓励采用NAMs进行早期去风险化,加速IND申请 [4, 8, 9] |
允许使用非动物数据,但行业强调动物模型仍是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必需品” 8 |
4 |
|
国际指南 (EMA/ISSCR) |
提高大型治疗产品的转化率和安全性 18 |
认可NAMs在早期筛选的价值 17 |
推荐在后期开发和关键研究中使用大动物模型来评估功效、剂量和安全性 18 |
17 |
VI. 结论:替代方法的定位与未来展望
6.1 现有NAMs是加速药物研发的强大工具,而非即时替代品
基于当前的科学证据和监管框架,关于细胞、类器官和芯片器官等新型替代方法已经可以完全取代实验动物的说法,在科学和监管层面是不能成立的。现有NAMs的价值在于其对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动物实验的巨大贡献。
NAMs通过提供更具人类特异性的数据(例如人类肝毒性预测),有效地弥补了传统动物模型在预测人体反应方面的科学缺陷 4 。它们是强大的早期筛选工具,能够对化合物进行高效、高通量的体外测试,从而大幅减少进入昂贵且耗时的动物体内(in vivo)研究阶段的失败化合物数量 3 。这种定位使NAMs成为传统动物模型的补充和先行筛选工具,提高了现有动物实验的质量和转化率 2 。当前的最佳实践是利用NAMs的精准局部信息来优化并减少所需的动物实验,这是在满足伦理要求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科学严谨性的务实路径。
6.2 实现绝对替代所需的科学突破方向
“绝对替代”是一个有待实现的远期科学目标,它要求替代方法能够模拟并预测活体动物所能提供的所有关键信息,特别是涉及全身稳态和动态代偿的复杂系统级数据。
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的研究方向必须集中解决NAMs的结构和功能性障碍。这包括:成功实现类器官的长期、稳定的血管化;将完整的、功能性的免疫细胞群整合到微生理系统中;以及创建可重现、可长期维护的综合多器官系统(MOOCs),以模拟药物在体内完整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清除路径 10 。
只有当NAMs的技术突破能够使它们展示出与活体动物相似或更优越的、系统级的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预测能力,并且其标准化和可重复性达到监管机构对终极安全验证所需的严格标准时,监管机构才能科学地、负责任地消除对动物模型的依赖 22 。目前的科学进程正处于从Reduction向Absolute Replacement迈进的漫长过渡阶段,绝对替代的实现仍需要重大的科学和工程突破。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Doke, S. K., & Dhawale, S. C. (2015). Alternatives to animal experiments: a review. Saudi Pharmaceutical Journal, 23(3), 223–229.
DFG Senate Commission on Animal Protec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2020). The 3Rs Principle and the Valid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NIEHS. Reducing the Use of Animals in Testing.
FDA. (2024). Roadmap to Reducing Animal Testing in Preclinical Safety Studies.
Animal Welfare Institute. The 3Rs.
Gessner, P. (2018). Large Animal Models i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 Paradigm Shift is Needed for Advanced Therapeutic Medicinal Products. 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6, 972.
Fritsche, E. et al. (2020). The role of cell-based in vitro models in the reproducibility of biomedical research. ALTEX, 37(1), 115–125.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6). Evaluating the Health Risks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 Interactive Handbook.
Hubrecht Organoid Technology. GI Toxicology.
Hutter, L. G., et al. (2023). Moving beyond the rodent model for drug discovery in Alzheimer’s disease. Frontiers in Molecular Neuroscience, 16.
Zompetta, C., et al. (2021).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 Complex Barrier for Cancer Immunotherapies. Cancers, 13(17), 4272.
Wang, X., et al. (2023). Future Directions of Organoid-on-a-Chip. Micromachines, 14(11), 1980.
Elveflow. Organoids vs Organ-on-a-Chip: Comparing 3D Models.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2025). FDA phasing out animal-testing requirement in some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es.
Thompson, S., & Hughes, T. (2019). Stem cell models as an in vitro model for drug-induced toxicity. Biochemical Journal, 476(7), 1149–1166.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imal Models.
Eder, K., et al. (2012). The need for more translatability in cancer research. Clinical & Translational Oncology, 14(8), 619–625.
Anbarasu, C. U., et al. (2023).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ver microphysiological systems for personalized medicine. 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11.
Inventia Life Science. The Reproducibility Dilemma: 2D vs 3D Models.
laojuyue
请到「后台-用户-个人资料」中填写个人说明。
© 2025 睿晏(杭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ICP备2025163781号-1  浙公网安备33010802013849号
浙公网安备33010802013849号